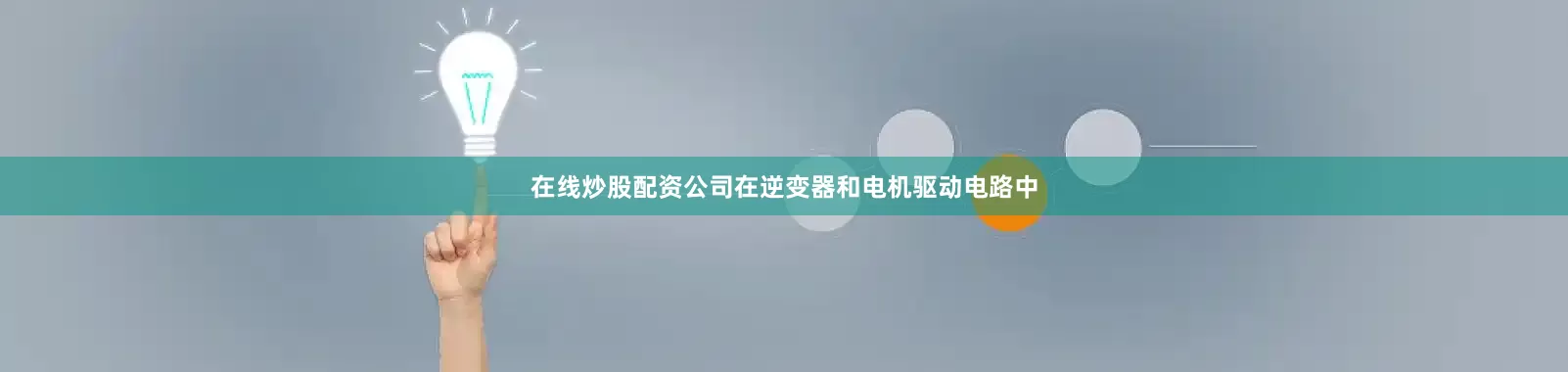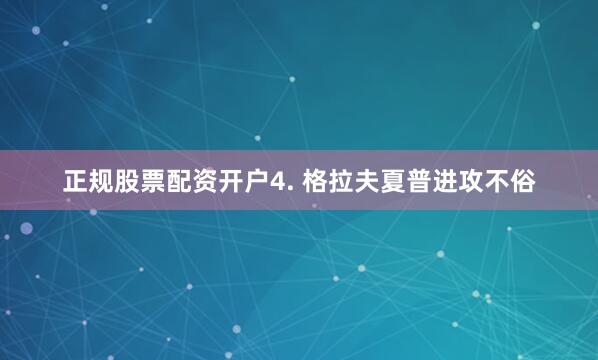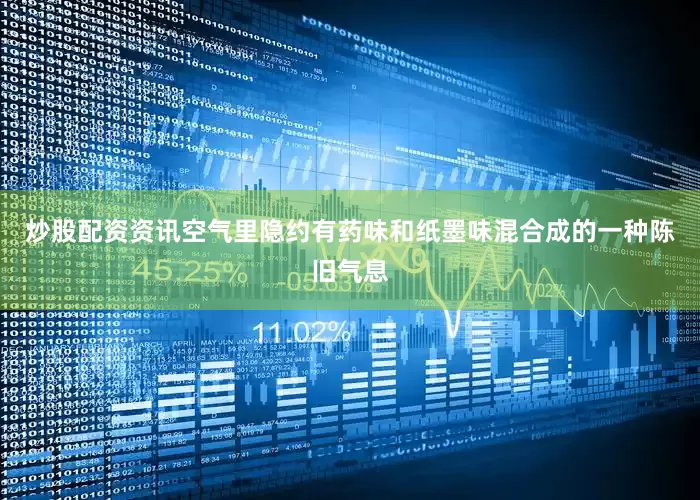
1974年中南海与人民大会堂的两次会面,李政道坐姿的微妙变化


五月底的北京,天色还带着初夏的薄凉。那几天城里风声紧,人们嘴上不说,可都知道局势并不平静。李政道住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套房里,窗外是长安街上稀疏驶过的公共汽车——车身漆色有些斑驳,售票员探出半个身子吆喝着下一站。他已经二十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景象了。


5月24日那天,他去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见周恩来,总理比他想象得更瘦,但精神很足。一开口就提起1972年他带回来的资料,说“我让中科院印成小册子了,不少人传阅”。话音轻快,却透着一种真心实意关切科研细节的劲儿。这让李政道心头一松,下意识翘起二郎腿,把手搭在沙发扶手上,说话也像和老同学闲聊似地快了起来。他直接抛出了“人才断档”的问题,还递上一份建议书——总理拿笔圈点,一边吩咐秘书转给教育部和科学院研究。这一幕,被随行摄影师捕捉下来,那张照片后来在不少物理系办公室墙上挂过。


六天后清晨,北京饭店电话骤响,把他从浅眠里惊醒,是外交部通知:一个小时后去中南海菊香书屋,毛主席要见你。他匆忙洗漱、换衣服,没有翻箱倒柜找资料,只是在脑子里反复推敲该怎么把建议说得简明而有力。秦惠箬替他整了整领口,说:“别急,你一直就是为这事回来的。”


菊香书屋里的光线被厚重窗帘滤得很柔,空气里隐约有药味和纸墨味混合成的一种陈旧气息。据九十年代某位老警卫员回忆,那阵子毛主席眼睛不好,看文件时要凑近,但握手依然用力。“早就听说你宇称不守恒那个发现,很好。”主席开门见山的话,让场面热络起来。然而落座时,李政道却挺直脊背、双脚平放、双手叠膝,这不是拘谨,而是一种本能敬意——对方不仅是国家领袖,更可能左右基础科学未来走向的人。在谈到“先搞应用还是培养基础科学人才”这个争议时,他注意到主席频频点头,这意味着他的观点至少被认真听进去了。


插一句旧事:安徽地方志《庐州续记》曾写到,“士之习艺,当自幼定志”,虽然原文指的是木工铁匠,却恰好契合少年班理念。不知李政道是否读过类似文字,但1975年再次来华时,他已将少年班方案细化到了考试科目与实验时间分配。当年的科技主管方毅看完方案,只问了一句:“这些孩子,会不会太小?” 李笑笑,“思维方式才是关键,不是年龄。”


1978年春,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招生启事贴出来的时候,有学生家长偷偷跑去校门口打量那些提前录取的小孩儿,有人摇头感叹:“这比我们村娃娃识字还早几年呢。” 那一年最小的新生才11岁,如今很多已成物理学界骨干。而这一切,都能追溯到四年前那两次会面间,一个科学家关于“断档”的执念。


后来,中美建交后的CUSPEA计划,又像是一条暗渠,把国内年轻学子的路引向世界前沿。有位参加首届考试的人跟我说,他们当年考题上的英文说明纸质粗糙、印刷模糊,是北大物理系老师用蜡纸刻出来油印的——可即便如此,也挡不住他们眼里的光亮。从1981到1998,那条渠送走又迎回来许多人,其中不少名字如今常出现在国际期刊封面作者栏上。


再往后,就是基金会资助留学生,还有零星寄语飞越太平洋抵达合肥或北京。但这些都是别人眼中的履历表,对当年的亲历者也许只是一次次坐下聊天、一封信、一台微型计算机、一摞泛黄文献那么简单而具体……就像我外祖父常念叨的一句老话:“树苗栽下去了,不必天天盯,它自己知道朝哪边长。”


配资推荐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长沙炒股配资公司适当地吃点油脂脂溶性维生素需要油脂辅助吸收
- 下一篇:没有了